《美麗閣》 暖色調香港

畫家夏加爾以善於運用色彩著稱,他的名作《紫羅蘭公雞》,整個畫面的基調和背景是一大片獨特的藍色,靜謐、深邃、憂鬱,如同午夜的天空、五百米海水的深藍和神秘幽深的夢境。然而,如果你仔細分辨,那層層疊疊大面積覆蓋着的藍色裏,隱隱散發着光芒的還有不同層次的紫色、粉色、綠色甚至還有紅色,它們混合在一起將原本清冷的藍色改造成了一種奇異的暖色調的藍,而這暖足以溫柔你的夢境。
周潔茹的新書《美麗閣》由16篇題材各異的短篇小說集結而成,其中前8篇可以說是「在香港」系列,後7篇以美國加州與紐約為背景,最後一個故事則是發生在作者的故鄉——常州。這樣的安排並非無意,《美麗閣》中的小說,除卻寫於2015年的《佐敦》,全是近兩年來的新作,而2015年,恰恰是周潔茹回歸寫作的時間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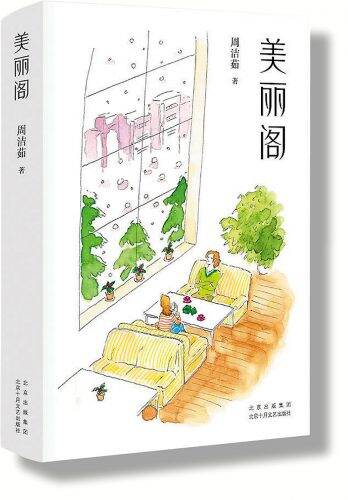
為什麼要從夏加爾說起,似乎並沒有什麼必然的聯繫。過去的時光裏,周潔茹在世界各地遷徙、流動,而她自己也始終像一個生活的漫遊者,到哪裏去,住在哪裏,觀察、書寫哪裏。周潔茹的故事裏有濃重的空間感,卻沒有確定的時間感,在漂泊中定居,又不知道哪一天可能隨時就會離開。因此,住而不定,在而疏離,在邊緣往復而不徹底融入,這和周潔茹的自我認知也不無關係,她曾在訪談中自我陳述:「我現在住在香港,我寫作。我肯定會寫與香港有關的作品,但是不會只寫這些,江南記憶和留在美國的青春,都是更珍貴的資源。」
「在既有規範和價值判定中不斷質疑並保留天真的生活態度」,這是周潔茹筆下人物的特點,也是周潔茹自己的生活姿態。而我想表達的重點是,周潔茹的香港書寫,看似冰冷的憂鬱的焦慮,茫然無措的碎碎念,一蔬一飯都是對香港經驗的敘說,對香港街區、道旁小店不厭其煩地一舉一動的描述,是對香港生活的愛與執着的表現。「我生活在香港,我觀察香港,我思考香港,我書寫香港,我愛香港。我愛的香港。」訪談中的她是如此堅定:「我覺得我就是香港人,新香港人。」所有關乎或者不關乎「香港人」的寫作,都來源於生活中的經驗和心中的感受,在流動中得心安,在破碎中求圓滿,在冷峻中見一絲暖色,在無地彷徨中尋找堅持。
冷靜凝視「新香港人」
《美麗閣》表現「新香港人」的香港經驗,卻不再只將目光停留在那些「優才」計劃的精英或者上層社會生活優渥的全職太太,還有靠七年等待的單程證才能在香港生活的底層新移民女性。周潔茹用刀片一般鋒利的語言將那看似完美富足的生活解剖開來,甚至無情地戳破這層光鮮亮麗的假象,呈現出庸常生活裏的虛偽、困頓、無奈、傷痛、虛無。「香港當然給你眼淚,香港也給你喜悅。」看似冷靜節制的情緒裏透露的是那種無法融入的邊緣感和失重感。

「我們為什麼要來香港呢?珍妮花說,又不是我們的故鄉。」「不是自己的地方」的寄居感,似乎又不僅僅在香港,「我的名字裏沒有E。珍妮花只是我的英文名字,我身份證名字裏沒有E。」這種輕描淡寫傳達出一種徒勞的不確定感,沒有的僅僅是「E」還是一些別的什麼可以讓我們安身立命的東西?而作為底層新移民女性的阿麗、阿芳、阿珍、阿May們,即使舉步維艱也不肯認命地努力生活,「新移民的仔也考得入香港大學」,阿珍對自己說。大概咬牙堅持、心存嚮往,就是意義所在。「來香港三十多年」的墨鏡女人,堅硬的假名牌包包,華麗優越的外表之下驟然撕裂的是不堪忍受的瑣碎、難以逾越的隔膜、漫無止境的消耗和無處遁形的游離;而走過台階的傍晚,喧囂的渡船街,上工的中西藥房,打過卡的眼淚,爬在手臂上的黃蜂,都是困頓中的守望。
無疑,周潔茹的寫作是自我的言說,是個人化的、情緒化的,甚至在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中年認命的蒼涼中仍然延續了一絲青春期的叛逆。她那些以異鄉為背景的新移民女性生存與情感的故事,無論是底層女性,還是小資情調的中產女性,她們似乎都在和世界和自我無聲地纏鬥、掙扎、努力。以香港為場域的作品當然是在地化的寫作,而那些以加州、紐約,以常州為背景的故事裏,又何嘗不是影影綽綽地能看見那一個「新香港人」的影子。寫作的重心也許從來都不是地域或者城市,而是生活在這裏的人們。
矛盾的閱讀體驗
閱讀周潔茹的文字,是一種矛盾的體驗和自我挑戰。一方面,她自顧自說話、表達的方式如同意識流,隨意而輕率,你可以跟着她的文字如影隨形,放任感覺漫無邊際地延展或者盤桓;另一方面,又是舉步維艱、需要不斷復盤的,如果你希望理解那些字裏行間的真實。在這種看似渙散、清淡、刻意重複的文字裏其實浸潤着的是循環往復的緊張、驚惶甚至焦灼,小說基本靠簡潔的似乎不相關的對話推進,沒有完整的情節也沒有完整的人物,她們一個個都似乎橫空出世又憑空消失,不解釋來由也不負責交代去處,她們面目模糊、語言相似、秉性相近,她們自說自話也並不期待互相理解卻又在莫名接續裏莫名擁抱取暖、相互慰藉。這些文字是周潔茹在自己一絲不苟的記憶中擷取的切面,是她多年來確認自我、認識世界的堅持和努力,是對無所事事、庸常世俗生活不肯屈服的逃離、對愛情對精神世界近乎絕望的渴求。
身體的傷痛和不自在,實際上是心靈的尷尬和不斷逃離。「房子」對周潔茹來說有着特殊的意義,而在她用文字構建的房子裏,從香港到加州到紐約到常州,似乎是從一個房間穿過另一個房間的轉場。異鄉是作為背景存在的生活場域,她倒並不很在意所謂身份的認同。《美麗閣》中的主人公似乎可以分為三類不同社會階層的人群,底層艱辛的打工女性、小資的文藝女中年還有「我」和「我」世界範圍內的閨蜜們,她們同樣面臨着島嶼上漂浮的人生和人到中年所遭遇的失意、尷尬,無處突圍的情感困境,以及無處安放的蒼涼。不同的城市名稱,相同的是周潔茹標誌性的都市書寫中那份迫切、慌張、不安、迷茫、尷尬與困惑,她們如同一個又一個美麗的標本,被集結於這一文學場域中的「美麗閣」展示。其實無論是阿珍阿芳還是珍妮花、林達或是「我」,她們雖然生活在社會的不同層面,做着不同的工作,呈現着各異的面向,然而,在本質上,她們面目模糊的身體裏住着的是同一個靈魂,她們是作家筆下一組經歷中年危機的女性群像,也是青春期叛逆的「美少女」作家在經歷了真實世界的塵世生活之後,在出走與回歸之間的自我確證與重建。在茫茫的螢火與星光下,在她們形形色色的生活裏,在她們的迷失、尋找與堅持中,她們被作家看見,也看見了作家自己,而我們,也在周潔茹有距離的審視和悲憫的反思中看見這暖色調的香港。
作者: 湯俏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
來源:大公文匯網





